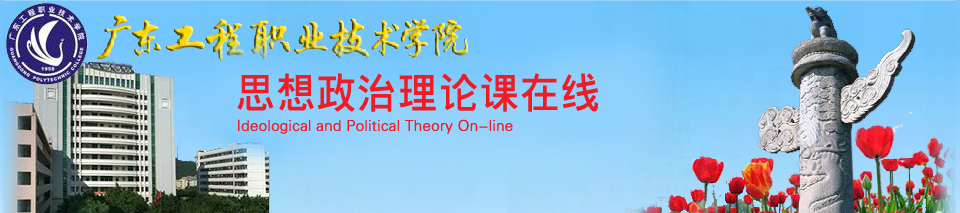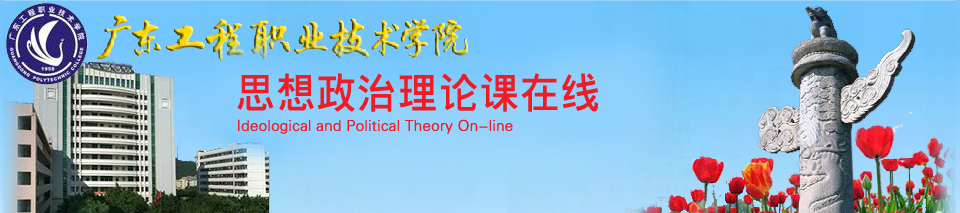2012年9月10日来源:中国教育报
■师魂·放歌
你是万千桃李永远的怀念
你是人们心中最美的名字
在我们最深的梦里,最放不下的始终是养我们的父母和育我们的老师。轻轻唤一声“老师”,今天是你的节日,我们想为你画一幅像,也许稚嫩的笔无法精确描摹出你对我们的师恩,但我们想说,你在我们的记忆里永恒!
编者按:
世界那么大,记忆那么长,多少往事、多少人物都已成过眼烟云,在我们最深的梦里,最放不下的始终是养我们的父母和育我们的老师。轻轻唤一声“老师”,今天是你的节日,我们想用我们的记忆为你画一幅像,我们稚嫩的笔也许始终无法精确描摹出你对我们的师恩,但我们想告诉你,你的师魂确已在我们的记忆里永恒!
师魂永恒
■肖敏
这是一个地图上
找寻不到的偏僻山村,
村里穷啊,就连鸟儿
也不愿飞来做窝
更找不到麂子
歇息饮水的蹄痕。
学校就是一间土屋
土墙斑驳,四下蒙尘,
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姑娘
刚刚毕业,就从城里
一脚跨入山中,这道
无框无架的校门。
乡亲们说,仙鹤
飞来还要飞走
从来没有城里教师
来这里落脚扎根,
更何况,这个娇美得
鲜花也似的年轻姑娘
城里还有当官的亲人。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个姑娘却像山花
绽放生命的美丽
并不需要几多养分,
当然,是否坚守
大山深处这个小小讲台
姑娘确实没少流泪自问,
只是,一咬牙,山竹
已经摇落了五度秋春。
乡亲们开始巴望仙鹤
不要飞走,因为山中
实在不能没有
梦寐以求的琅琅书声,
更少见,如此
掺沙摸泥的玉壶冰心。
于是,隔三差五
就有人为姑娘
送一篮土豆、两棵白菜
或是在门边放几支青笋
贫穷的山里乡亲
豆棚瓜架的心地
就是这样表达
泥土风味的温存。
不料这些日子
暴雨连降,山洪滚滚
教室墙体突然坍塌
姑娘平淡的心怀
陡然发生掀天巨震:
“学生、学生重于泰山”
她连喊带拉,赶着
孩子们离险逃生,
紧急中一回头,哎呀
一个双腿残疾的孩子
满脸惊骇,难以起身;
眨眼间,姑娘一闪而至
猛地急甩,孩子绝地脱困
姑娘却被狂泻的泥流
埋得很深、很深。
姑娘没有英模称号
却有一个山崩地裂
也不会变的教师身份,
她的洁白的生命
从此化为山中
一抹常青的绿茵——
守望山乡的永恒师魂!
报师恩何须待功成
人物:陈老师,城镇教师
速描:热爱学生,为解已毕业学生心结,在电话还不普及的年代坚持隔几天就打一个电话劝慰、鼓励
■刘亚华
19岁那年,我正读大一,父亲的陡然去世,让我茫然不知所措。亲情的缺失,前程的渺茫,让我总是在半夜里,莫名其妙地哭醒。后来,为了排遣心头的忧郁,我想到了写信。
写给谁好呢?就写给陈老师吧。高中时,他一直对我特别关照,不仅像慈爱的父亲般温暖,而且像朋友一样可以倾心交谈。
信发出去后,很久没有音讯。我猜想,陈老师教学任务重,回信看来是没有指望了。就在我将要放弃这段盼望的时候,陈老师的电话打了过来。17年前,电话还是稀缺之物,他是打到我们学校教导处的。陈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调到邻镇的学校任职,信辗转了好久才收到,得知我的遭遇,他很同情,但他激励我,人要勇敢地面对一切,他相信,我的明天会辉煌灿烂。
听了老师的一席话,我如沐春风,心里顿有一股积极的能量,变得热情开朗起来。怕我灰心,陈老师每隔一个星期就会打一个电话鼓励我。每次接完陈老师的电话,我都兴高采烈、信心满怀,我期待我的未来真像陈老师口中说的一样,功成名就、辉煌灿烂。
陈老师就这样鼓励着我,虽然从来不写信,但坚持隔几天一个电话,热情洋溢的话语总会激励我好久。
在当初最艰难、最彷徨的日子里,是陈老师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让我像一张鼓满了风的帆,努力、积极、充满热情。
我去了广州,在一家不大的公司从基层做起,后来工作不顺,又辗转了几家公司,事业没有任何进展。起初,我还给陈老师打电话汇报情况,但后来诸多不顺,让我有些无颜面对他。
今年春节,我终于鼓足勇气,去见了我恩重如山的陈老师。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陈老师脱口而出叫出了我的名字。谈及我现在的境况,老师满脸笑意地说:“有一个幸福的家、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就是我最高兴的。”
我也终于笑开了颜,何须功成名就报师恩,老师的心愿其实很简单: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幸福。那错失的17年,其实我本可以给老师带来无数的欢笑。
老师为我家当“苦力”
人物:李老师,从城市到乡村任教的教师
速描:认真负责,为学生不耽误学习帮学生家里干苦活
■李金鹏
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当这个日子临近,我都会想起童年的贫苦经历,还有充当我家“苦劳力”的李老师。
我的老家在山区,那个时候经济条件相当落后,村里能上得起学的孩子不多。父母多种了几亩大枣,从牙缝里挤出钱供我读书,但地里的活实在太多,如果遇到农忙时,我就不得不暂时放下学业,回地里帮大人的忙。
小学二年级,山区里来了一位又高又瘦的老师,姓李,长得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同学们在私下都管他叫“筷子李”。那时我们想,原来城里也有吃不起饭的人啊,怎么瘦成这样呢?
农忙时节,我不得不放下书本,跑到田里帮工,一连几天没上学。李老师知道了情况,很严肃地说:“怎么有这事!”我一听,坏了,“筷子李”这是要发飙啊。但出乎我的意料,李老师手一挥说:“明天,我去体验体验生活。”
第二天,李老师和我到了田里,父母以为是老师来找家长算账,正要开口解释,却见李老师拾起工具干起活来,弄得我们一家人都不好意思。整整干了半天,李老师这才有空喘口粗气,对父亲说:“大叔,家里的活确实忙不过来,这样吧,每天下午放学,我来地里帮忙,白天就让他安心读书吧。”
于是,李老师每天放学,都会和我风驰电掣地奔向农田,因为多省一点时间、多干一点活,我就可以少耽误一点课程。李老师毕竟是城里人,哪里干过那么累的农活,两三个星期下来,李老师更加消瘦黝黑了。
因为地里有李老师的帮助,我耽误的功课非常少,后来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镇初中,一向感情不外露的李老师也忍不住喜笑颜开。
离校那天,李老师送给我一双筷子,并开玩笑说:“给你一双筷子,这是有寓意的,一来呢,你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筷子’,二来呢,筷子是吃饭的工具,你要争气多学本事。”
时光荏苒,生活中的许多琐事都已忘记,唯独李老师充当我家“苦劳力”的事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救险”老师
人物:李合香老师,初中语文教师
速描:细心关注学生感受,真诚爱护学生
■毛海红
在我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教过我的老师数十名,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淡出我的记忆,唯独李合香老师深深地刻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使我铭记终生。
李老师是我初一时的语文老师,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同在一所高中教书,两家关系不错。我上的中学离家较远,李老师就让我陪她一起住在学校里。
我患有气管炎,每到冬天就咳嗽不止,晚上吵得李老师也睡不好觉,她三番五次起来给我倒水吃药。最难为情的是,我一咳嗽就小便失禁尿在床上。我怕老师发现笑话我,就用身子贴住尿湿的那片,企图把它暖干,可我的身子洇得红红地出了疹子,床单褥子依然是湿湿的。
下课后,我发现我的被褥已拆洗得干干净净晾晒在操场上,李老师正在翻晒棉花套。当我的目光与她相遇时,我迅速地逃开了,脸也一下红了。李老师却说是她叠被子不小心打碎了“暖水瓶”(那时乡下都用医院输完液的空瓶子装热水暖被窝),被褥弄湿了,就顺便拆洗了。
冬天,小屋里很冷,为了取暖,李老师在屋里生起一个煤炉,架上烟囱通向窗外。有一天夜里风很大,烟囱的出烟方向和风形成逆流,致使煤烟被风堵了回来灌进屋里。我睡得昏昏沉沉,只觉得头有点疼,想动,四肢无力,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骨碌儿爬起来就往外冲,我要去找李老师!在门口,我与李老师撞了个满怀,看到李老师平安无事,我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原来那天夜里,李老师也感觉到头疼头晕,她凭经验知道是煤气中毒了,赶紧起来开门窗,可是浑身无力,一起来就跌倒了,她用尽全力爬到门口把门打开后,就晕了过去。过堂风很大,门被风关上了,李老师也被关在门外,而我被锁在屋里。阵阵凉风袭来,李老师醒了,她敲门叫我开门,可我早已失去了知觉,后来在邻居老师的帮助下才把门撬开。我被及时地送往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是李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转眼我离开学校已20年了,教师节快到了,在此给李老师送上我真诚的祝福: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幸福!(作者单位:河南洛阳河柴重工特螺公司)
“万能”老师王文贤
人物:王文贤老师,多年民办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
速描:在艰苦条件下坚守30多年、什么都能教的老教师
■王新芳
又是教师节,近来常常忆及小学老师王文贤。王老师是本村人,从民办教师到修成正果,一干就是30多年。村里很多家庭,从父亲到孩子都是王老师的学生。而我,也是他众多弟子中的一个。
最近晚上做梦,总是出现放了学回家的情景。恍如隔世的30年,一切似乎都遗忘了,可一梦见,又真切如昨日,能触摸到童真的心跳。
简陋的办学条件,并没有束缚住老师的教学才华。他能在顶着立柱的教室里领着我们高歌“社会主义好”;在温暖的墙根下,为趴在凳子上的我们讲解数学;上体育课,我们排着队,去野外寻找一条近百米的田间直路,老师吹响哨子,我们就如离弦之箭展开了短跑拼杀。在我们小小的眼里,老师是万能的,他什么都能教。一年级、三年级的复式班,或二年级、四年级的复式班,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而且课上得灵活生动、有声有色。为了让我们懂得杠杆的原理,他从家里扛了一根粗木棍,带领我们到学校后的石头堆旁,摩拳擦掌,在我们好奇的观战中,撬起了一块足够大的石头。
老师很具亲和力,在物质贫瘠的岁月中教我们快乐学知识,让教师这一职业充满圣洁的光辉。但是,有时候他又是认真而严厉的,有一次的作文指导,就让我时时想起、时时惊心。
村里新打了一眼机井,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我喜欢作文,而且喜欢“拽词”。老师让写美丽的家乡,我得意地描写了机井周围的景色,写了那芦苇荡深处的野鸟,采苇叶姑娘的欢笑,最后还用了一个词概括——“一饱眼福”。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怀着忐忑的心情听老师指导。他问我“一饱眼福”是什么意思,我窘迫地答不上来。老师又问我从哪里知道的这个词,我不敢撒谎,老实回答说从一本作文书上看来的。老师严肃地教导我,这个词用得好,并没有用错。但是今后注意,用词不能乱用,一定要先明其意。我诺诺而退,对作文多了份严谨和责任。
往事一直在灵魂深处安睡,偶尔一天醒来,时光已经把很多所谓大事消磨殆尽,而它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沉沉地就有了无比重量。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每逢回村,也会碰到王老师正走在放学的路上,在黄昏里打个招呼匆匆而过。淡淡的背后,是内心对老师的尊敬和感激,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我幸运地遇到了王老师。(作者单位:河北省内丘县职教中心)
老师教我“快乐成长”
人物:汪老师、俞老师,代课教师
速描:与学生打成一片,带领学生一起快乐求知
■方根秀
“a,一个小圆圈上长个小尾巴;o一个小圆圈没有小尾巴。我们有没有小尾巴啊?”这是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汪老师在教我们写拼音字母。为什么时隔这么久,记忆还这么清晰,因为我的回答闹笑话了:“有!”老师问我尾巴在哪,我毫不含糊地指指头上的小辫子。老师的嘴角往上一翘,笑着说:“那是辫子,不是尾巴。记着,人没有尾巴了。”
那是个教学点,两间土墙灰瓦房,两块黑板,两张小办公桌,两位年轻的代课老师,一群来自3个小村子的孩子,一些大小不一自家带来的凳子,两个年级。汪老师教我们一年级语文和二年级的数学,另一位俞老师教我们数学和二年级语文。
记得入学第一天,老师带领我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我们的凳子尽可能地摆放整齐。后来每到新学期开始,没等老师发话,我们就自动从附近的同学家里拿来用具扫净教室、擦亮黑板。老师乐得眉开眼笑,竖起大拇指,夸我们懂事。早晨,我们经常抢在老师之前到校,一人坐在门槛上,再一人坐在他脚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坐下,掏出语文书摊在前面同学的背上开始读起来。老师来了还是眉开眼笑地竖起大拇指。
我们要上音乐课,汪老师就教我们唱歌,她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我们闹着要上体育课,俞老师就找来绳子教我们跳。后来还花钱买来两个足球带我们踢。
课下我们也总黏在老师身边,特别是冬天,俞老师带男生围圈跑步,汪老师就带我们在圈子里踢毽子跳绳。有时,两位老师分别带两拨同学,举行跳绳或踢毽子比赛,最后总是不相上下,分不出输赢。秋天,老师陪我们在学校后边的树荫下背书。我们一边背,一边看蚂蚁搬家,看树上垂下的卷起的叶子里躲着什么样的虫子。然后轮流背给老师听,过关了先玩耍,过不了的继续背,背会为止。
学校旁边还有小池塘。老师到塘边洗手,我们跟着到水边。老师说:“我还说人没有尾巴呢,你们都成我的小尾巴了。”我说:“长大我也要当老师,我也要许多小尾巴。”
读完二年级要离开教学点了,我们恋恋不舍,对两位老师,对那个教学点。其实,我们留恋的是那种学习生活的状态:老师跟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我们整天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不知“压力”为何物。
儿时当老师的梦早已实现。教室窗明几净,多媒体班班通,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动听的音乐铃声,塑胶跑道,这一切跟我儿时的学校有着天壤之别。而我面对的总是六七十人的泱泱大班,我就特别怀念那个教学点,怀念我的两位启蒙老师……(作者单位:安徽芜湖许镇中心小学)
平凡辛老师,走好
人物:辛开岚老师,工作几十年的民办教师
速描:严格而不失温柔,夫妻两地分居但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几十年
■阮华君
总也忘不了我的小学启蒙老师——辛开岚。她那时大约30岁左右,住在我家西边毗邻的一个小村里。她并不是那小村里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外地嫁过来的。
她的丈夫姓万,自我懂事起,就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他是我家周边几个小村里父老乡亲口中的神话。
当年,他参加高考,那时还不是全国统一考试,他同时考上了一所解放军指挥学院和一所医科大学。如何取舍,他也拿不定主意,就回家征求父母意见。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觉得上军校当军官是不能做一辈子的,学医是一项技术,可以做一辈子,还能传给子孙后代。于是力主他学医,他就去了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革命老区,他被分配到了安徽来安一个乡镇医院,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丈夫在异地工作,我的辛老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做民办教师,操持家务。
她原来也是考取师范学校的学生,尚未毕业,文革时一纸命令,学校撤了,学生各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她就成了民办教师。
她个子高高,不胖不瘦,直到四五十岁时身材也一直很好,五官端正,鸭蛋圆脸,出嫁前应该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脸上有很多雀斑。
她那时候教一、二年级,我刚上学那会儿,一、二年级还是复式班——即一、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她先教一年级,教完了布置作业让他们写,再教二年级。虽然学生总数不是太多,但烦心事却更多,经常是她正在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的孩子就打闹起来,她不得不停下,去安抚他们。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她讲课、读书、安抚学生、和不懂事的小孩磨嘴皮子、带我们读课文的样子。
她非常和蔼,对我们比母亲还温柔,从不像那些男教师凶神恶煞般,动不动就用棍子抽,用巴掌打我们。我记得不止一次,有学生喊她“妈……”。
那时,我们的课桌都是土坯支起的,很容易损坏。
有一年夏天,辛老师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技术,她指挥我们全校几十个师生和好黄泥巴,把一束束稻草弄成长条子,在和好的黄泥巴里滚上稀泥巴,裹上麻杆,平铺在地上,摆成课桌的造型,一层一层码上去,说是晒干了,扶起来就成课桌了。经过一天大干,看着躺在地上很有课桌雏型的成果,我们心里也很高兴。正梦想过几天就有新课桌了,有一天夜里,下了暴雨,第二天早晨来到学校时,一看就傻眼了,我们辛辛苦苦做的“课桌”早已被暴雨淋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点点“尸骨”,惨不忍睹。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做过。
在我小学五年当中,学校先后也来过一两位女教师,有的是下放学生,但她们工作时间都不长,总是一两年就走了,只有辛老师一直在那个乡村小学校工作。从她家到学校大约二里多地,都是窄窄的田埂小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她都是早上去,中午回,午后去,傍晚回。除了放假,她天天如此,风尘仆仆、匆匆忙忙,从冬走到夏,又从春走到秋,从新娘走成母亲,又从母亲走成祖母,拿着微薄的民师工资,夫妻常年分居,一人带3个孩子,操持家务,辛勤工作。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她那一批尚未毕业就遣散回乡的师范生,凡是从事民师工作的,一律转为公办教师,承认中专学历,我的辛老师才真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而她也接近退休年龄了。她丈夫90年代末也从山旮旯里调回了我们县城医院工作。
最近我回家探望老母,一再打听辛老师的消息,听到的是一个噩耗:3年前,辛老师在县城生病住院,被医生用错药致死。消息确证后,我心情无比悲哀。辛老师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乡村教师一员,一生辛劳,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撑起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天。
永远怀念您,我的辛老师。(作者单位:安徽省明光市张八岭中学)
我的“爷爷先生”
人物:“爷爷”教师,“我”的启蒙老师
速描:热爱教育事业,极其负责,全身心投入,桃李遍天下
■李庆益
在家乡,“先生”是个尊称,被尊为“先生”的人都是这一带颇有声望的老人。我的爷爷是一个教书匠,教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桃李满天下,乡亲们都管他叫“李先生”。
爷爷是从哪一年开始教学生涯的,我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刚开始是教当地的一间私塾。
作为家乡一带比较有声望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时百废待兴,教育战线人才更是严重匮乏,上级已经准备把爷爷调离家乡,放到城里更重要的岗位上去。爷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个消息,他找到了当时的负责人,说家乡小学师资严重不足,我还是留在这里吧。领导拗不过他的执着和热情,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他做了家乡小学的校长。就这样,爷爷留了下来,而且是一留一辈子,从此再没有离开过乡村小学。
那时小学的教学条件可真苦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师生们白天在校上课,晚上都得回家去住。从我家去学校的路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一路凹凸不平,还要撑竹排渡过一条没有桥的河。爷爷每天早出晚归,全凭一双铁脚走天下。夏天还好,可一到寒冬或者雨天就惨了,这段漫漫长路简直成了一座奈何桥,来也难去也难。爷爷没有丝毫的怨言,风里来雨里去,一批批学生在他的注视下展翅高飞了。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爷爷,他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数学。爷爷并没因我是他的孙子而另眼相待,全班小孩皆一视同仁。有一次,我贪玩忘了上课时间,待我发觉后为时已晚,爷爷把我堵在教室门口,板着脸教训我,罚我站在墙边听课,整整一节课不让动,害得我脚都站麻了。我倍感委屈,泪水哗啦啦地下来,爷爷却装作没看见。最尴尬的是,上课时学生要起立叫“老师好”,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叫才好,叫“爷爷”不行,叫“老师”又拗口,我只能愣在那里,张着嘴巴作个模样。有些家长知道了,调侃我说:“你应该叫‘爷爷先生好’!”
该退休了,爷爷仍舍不得离开讲台。有好心人来劝他,您老先生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了几十年,该好好休息了。爷爷激动地说,现在小学师资不足,我这一退谁来顶啊,趁我身体硬朗着,再带一两批孩子吧。
64岁退休那年,爷爷一下子瘦了,再也没有胖起来。以后很长一段日子,他还经常回到学校。他默默地坐在校园门口的石凳上,遇见学生、老师总是和蔼可亲。有些学生在课余时间会向他讨教问题,甚至还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来呢。爷爷时常在教室无人的时候,悄悄地走上讲台,嘴上念念有词,那样子,似乎台下仍是满满一堂的学生。小小讲台,已成了爷爷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一个秋风瑟缩的日子里,爷爷含笑走进了青山松涛之间,与他一辈子热爱的故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出殡那一天,乡亲们送来的花圈、挽联不但挤满了整个灵堂,还挨挨挤挤摆满了灵堂外的长走廊。前来送殡的人很多,有村里的乡亲、亲戚、学校师生、乡干部,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我问我父亲是否认识这些人,父亲摇了摇头,说爷爷教了半个世纪的书,那些大概是他的学生吧。
(作者单位: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胡老师的“最后一课”
人物:胡老师,远离家乡异地任教的教师
速描:教学技术高超,对学生充满爱,善于引领,深受学生热爱
■胡忠伟
20多年前,我在村子里读小学。记得入学第一天,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服饰整洁,穿着一双黑绒布鞋子,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他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在我们那个村小,可是开天辟地的事。他自我介绍说:“我姓胡,大家叫我胡老师,山西人。”
记得那一课是《绿色的办公室》,胡老师声情并茂地领读着课文,我们全被老师那浑厚深沉、充满磁性的普通话吸引住了。课文里写道,列宁为了躲避敌人,每天都要经过一段临渊的小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陡峭的山峰,列宁就那样面贴着山峰,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挪过这段小路。胡老师讲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列宁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和人民,住这么简陋的房子,忘我地工作,今天,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有何感想,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说完,胡老师用力在黑板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从此,胡老师领着我们20来个娃娃,徜徉在美丽的语文世界里,背课文、读诗歌、学说普通话,每一节课都充满了师生欢乐的笑声。同学们的成绩直线上升,以前那些不爱写作文、逃课淘气的孩子也爱上语文课了。在期中考试时,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平均分突破了90分大关,这让学校师生都很震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学校的语文成绩最高不到70分。为此,学校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总结表彰大会,我们班所有学生都从校长手里领到了一张奖状,胡老师在会上发了言。那一天是我们班最快乐、最幸福的一天。
就这样,胡老师带领我们一帮孩子,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有一天,班长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胡老师要走了,返回老家,再也不教书了。我们商量着怎样送别胡老师,大家七嘴八舌,说来说去,还是文体委员点子多,他建议,快要过中秋节了,一人凑5毛钱,给老师买一盒月饼吧。大家一致同意。我却在心里犯难了:这5毛钱,到哪儿弄去?父母为了我能上学,整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大姐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二姐只读到四年级,因为家里缺帮手也辍学了。我呢,除了念书还是念书,家里的活儿,父母根本不让我插手。一家人都这样优待我,我怎么还能给家里添忧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跟父母开口,提那5毛钱的事儿。
八月十五那天,我们班用最后一课为胡老师举行了欢送仪式,同学们每人唱了一首歌,胡老师也深情地唱了一首歌,还给我们讲了一段话,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出人头地。然后,班长将那一箱月饼恭恭敬敬地送给了胡老师。胡老师接过月饼,动情地说:“同学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月饼,还是大家吃吧。”说着,胡老师将月饼分发给大家,一人一块,刚好。接过月饼,我偷偷地看了看大家,没人注意我,大家都在吃,我就把它放进了桌兜里。第二天,胡老师再也没来学校,他已经走了。
一晃半月过去,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胡老师的事,我就原原本本地说了。听完我的叙说,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娃呀,胡老师对咱那么好,咱欠人家胡老师一个人情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来到教室,拿出那一块胡老师留给我的月饼,月饼已经发霉了,拿着发霉的月饼,胡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的一幕幕又一次浮上眼前:
有一次,我为了偷懒,在生字本下面铺了复写纸,一连印了好几张,胡老师发现后,他并没有当众责骂我,而是悄悄撕掉了复写的那几页作业,并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做人要真诚,勤奋出成果。”
胡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文章,教我读书,教我做人,他那浑厚而充满磁性的普通话,他最后一课的情形一直深深地嵌在我的心里……(作者单位:陕西彬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博师恩·
@咪咪老猫:30多年前,我记忆中的老师身着白色的衬衫,梳着短发,白皙的脸庞,一双大大的眼睛,给人一种威严又慈祥的感觉。她讲话多沙哑(很可能是为我们这50多个孩子累的)。小学毕业再没见到过她。很是想念!她叫詹景书,我终生难忘的老师!
@姚智颖:那个像爷爷一样亲切的语文老师,一直宠爱着我们的他,现在还好吗?身体是否还和以前一样硬朗?每天都开心吗?教师节又到了,真心祝福远方的您一切安好!
@欢欢:记得我的成绩很差,那次,你在全班同学面前鼓励我很聪明,只有我一个人用了简便方法。从那时,我爱上了数学,成绩突飞猛进……老师,也许你早忘了,可我却没有忘记,谢谢你,老师。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胡彬彬:说实话,最难忘还是我的高中老师,她真的特别好,对我们特有信心。不管我们多么地不爱学,她还是努力地教我们,我们也开始慢慢地喜欢上这位老师。她那么和蔼可亲,我们好幸福啊!她的名字叫张爱双,印象深刻。
@丁宏:教师节就要到了,我的学生生涯有几位难忘的老师,他们不仅传授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的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如何做有价值的人,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初中(92届河北张家口七中物理曾老师、语文王老师)、高中(95届武汉子女中学语文邓思治老师)。感谢你们!
@田鹏国: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岳老师要求我们每次看书的时候都在手里拿一支笔,记录下重点词语、优美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每次不管是看什么书,我都习惯了在手里拿一支笔,记几句有用的东西。小时候养成的好习惯,陪伴我走了20多个春秋。岳老师,您还好吗?
——摘自腾讯微博“感念师恩”